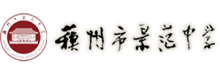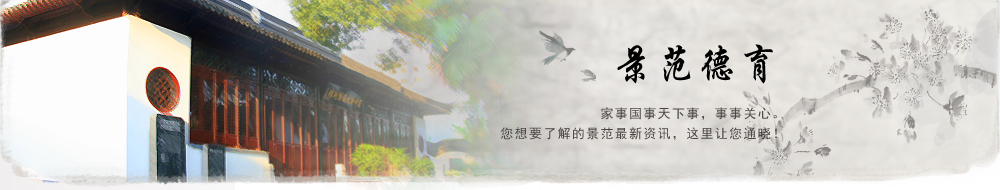你体验过焦虑吗?
假如明天,你要和暗恋已久的人第一次约会,此时可能是什么心情呢?假如明天,你有一场重要的考试或面试,而你又觉得自己尚未准备好,此时又是什么心情呢?
你兴许会感到兴奋、期待、跃跃欲试,同时也一定会有些紧张、焦虑、惴惴不安。事实上,我们大多数人几乎每天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,体验到不同程度的焦虑。
那么,到底什么是焦虑呢?
焦虑类似于我们经常谈到的“紧张”。焦虑是一种以消极的负性情绪、紧张的躯体症状以及对未来的担忧为特点的情绪状态。
焦虑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,有些莫名的担忧和烦躁,会坐立不安、失眠,甚至还会伴随一些生理反应,如声音发颤、心跳加快和呕吐等。既然焦虑如此惹人厌,为什么我们还要进化出这么一种情绪状态呢?
早在一个世纪之前,心理学家就发现,轻度焦虑有助于人们取得更卓越的表现(Yerkes & Dodson, 1908)。如果我们不会感受到焦虑,那我们可能就不会为约会、考试或面试而精心准备,最终很可能无法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。
可见,适度的焦虑是一种动力。可是,一旦焦虑过度呢?总不会是越焦虑,表现越好吧?
当然不是!过度或不当的焦虑不仅会干扰我们的日常生活,削弱社会交往能力,降低工作效率和工作表现,甚至还会提高我们患慢性疾病的可能性(Orme-Johnson & Barnes, 2014)。
更糟的是,严重的焦虑状态并没有那么容易消失,就算我们反复告诉自己,没有必要担心,也仍旧会被焦虑继续折磨着。
既然焦虑不可避免,焦虑“有好有坏”,那我们何不想办法与焦虑和平共处呢?想想看,为了克服焦虑,你都做过哪些尝试?
如何与焦虑和平共处?
今天,我们就来介绍一种经过大量科学研究检验、能够有效应对焦虑的方法——正念冥想。
正念冥想脱胎于东方佛教文化,是一组以正念技术为核心的冥想练习方法,有助于我们真正实现与焦虑的和平共处。
正念,就是将注意力指向当下目标,不加评判地对待此时此刻的各种经历或体验(Kabat-Zin, 2003)。
正念冥想则是一组以正念技术为核心的冥想练习方法,主要包括东方文化中的“禅修”、“内观”和西方文化中的“正念减压疗法”、“正念认知疗法”。正念冥想假设,逃避会加剧痛苦,允许痛苦地存在,并接纳痛苦是练习起效的重要机制(Germer, 2005)。
这意味着,我们既不要沉湎过去,也不要忧虑未来,更不要试图忽视或者回避此时此地。我们要做的是,不加评判地专注于当下,有意识地放任情绪、生理感受、想法念头等自由来去。倘若此时你感到焦虑,那就去观察它,去理解它,最终消除它,或是接受它。
图为乔·卡巴金(Jon Kabat-Zinn),正念减压疗法创始人,美国麻省大学荣誉退休医学教授,麻省大学医学院医学、保健和社会正念中心的创立执行主任,麻省大学医学院减压门诊的创立主任。著有《正念:此刻是一枝花》、《穿越抑郁的正念之道》、《多舛的生命》等。
正念冥想能够缓解焦虑的证据
研究者发现,正念冥想能够缓解疼痛、焦虑等生理和心理问题。那么,正念冥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焦虑?这种缓解能持续多久?我们尚不得而知。
因此,国内学者任志洪等(2018)对在2011年~2015年间公开发表的55篇有关正念冥想与焦虑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元分析(即“对已有研究的研究”,指对现有的实证研究数据再次进行统计分析),结果发现,正念冥想对焦虑干预的即时效果量为0.60,达到了中等以上的效果,但追踪效果量为0.29,是一个很小的效果。
简单来说,正念冥想能够缓解当下的焦虑,并且效果较好,只是缓解效果难以持续。这也告诉我们,正念冥想不是“一劳永逸”的,而是要时时练习,尤其是在我们被焦虑的阴影笼罩之时。
总之,正念冥想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具有长期影响,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焦虑,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觉察能力,近而提高我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(Gotink et al., 2015)。假如你又深陷焦虑而无法自拔,不妨试试正念冥想这种“无害”的心理健康自助方式吧!
参考文献
任志洪, 张雅文, 江光荣. (2018). 正念冥想对焦虑症状的干预: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元分析.心理学报, 50(3), 283–350.
Germer, C. K. (2005). Anxiety disorders: Befriending fear. In C. K. Germer, R. D. Siegel, & P. R. Fulton (Eds.), Mindfulness and psychotherapy (pp. 152–172). New York, NY, US: The Guilford Press.
Gotink, R. A., Chu, P., Busschbach, J. J. V., Benson, H., Fricchione, G. L., & Hunink, M. G. M. (2015). Standardised mindfulness-based interventions in healthcare: An overview of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-analyses of RCTs. PLoS One, 10(4), e124344.
Kabat-Zinn, J. (2003). Mindfulness-based interventions in context: Past, present, and future. Clinical Psychology: Science and Practice, 10(2), 144–156.
Orme-Johnson, D. W., & Barnes, V. A. (2014). Effects of the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technique> 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, 20(5), 330–341.
Yerkes, R. M., & Dodson, J. D. (1908). The relation of strength of stimulus to rapidity of habit-formation.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& Psychology, 18(5), 459–482.
注:本文转自公众号“国民心理健康素养”
|